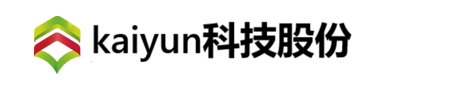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各学科年度研究成果,聚焦机器“传播者”主体确立、智能体崛起与“跨人类传播”常态化、智能传播对社会变革与治理的影响、智能传播与国际传播的互动、智能传播的具身转向及物理世界嵌入、人机共生的治理路径等关键议题,描绘 2025 年智能传播主流化元年的研究图景,为构建相关新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技术倒逼学术,是互联网浪潮兴起30多年来,实践与理论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2025年12月11日,《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荣誉授予“AI建设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深度求索首席执行官梁文锋等多名中国企业家入选 “2025年度全球AI领域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杂志进一步指出,2025年关于“应否谨慎释放AI”的争论已让位于“尽快部署AI”的竞赛。[1]这一历史性的定格,与《时代周刊》过往的两次标志性评选构成了深刻的互文。1982年,“个人电脑(PC)”当选年度风云人物,确立了数字化时代的物理基座;2006年,“你(YOU)”的登顶宣告了互联网主体权力的下沉,标志着个体成为网络世界的主导者。如果说1982年和2006年分别开启了计算时代与网络时代,那么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通过极致的架构优化与成本控制,确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DeepSeek时刻”,构成了智能传播技术主流化的关键拐点。[2]将2025年定位为“智能传播主流化元年”,是其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的关键标识。作为对时代变革的回应,2025年也开启了智能传播学术研究的新阶段。
开源是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创新的重要模式,但不是所有开源模式都可以获得成功。[3]DeepSeek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参数规模与算力竞赛上,更在于它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以此为标志,长期阻滞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成本壁垒被有效消解,高性能AIGC具备了普惠化与基础设施化的可能,在低成本与高性能间打通了价值实现的“最后一公里”。[4]由此,以AIGC为基础的智能传播也获得了跨越“创新鸿沟”的关键驱动力。随后,Meta发布Llama 4系列、华为推出盘古Ultra MoE、Google DeepMind发布Gemini 3,一系列技术应用的爆发,配合英伟达Blackwell GPU等底层算力的普及,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共生、技术平权的智能传播新生态。智能传播真正作为一种主流范式,深入主流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了与当前强势的社交传播范式分庭抗礼、争夺未来主导权的新格局。
依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2025年,智能传播结束了由“创新者”与“早期采用者”主导的试验阶段,开始进入“早期大众”接纳的历史新周期。在“AI一天,人间一年”的背景下,AI从特定技术圈层的专属工具,逐步转变为一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通用生产力工具。一系列数据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资本市场的价值共识率先确立了智能传播的主流化基座。2025年10月,OpenAI完成员工股份二级转让,公司估值飙升至5000亿美元,一举超越SpaceX(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5]这一里程碑事件表明,全球资本已将人工智能看作下一代核心生产力的坚定布局与押注。在生产力工具化层面,AI已深度嵌入职业场域。Google Cloud发布的“The ROI of AI 2025”报告显示,生成式AI显著提升了企业效能,其中IT流程与非IT流程的生产力,分别提升了70%与60%;[6]Prialto的“2025 Executive Productivity Report”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约有78%的高管已将AI纳入日常工作,视之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力工具。[7]在生活常态化层面,AI的使用场景完成了从“尝鲜”向“日常”的结构性迁移。数据显示,普通人的“AI时刻”(实际使用体验)占比,较上一年增长约9倍,[8]但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其渗透的广度——从互联网搜索、个性化购物到流媒体娱乐及智能家庭助手,AI已成为年轻一代获取技能与丰富生活的重要工具。[9]特别是在中国市场,这种常态化渗透率的增长尤为显著。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与应用场景的拓展,公众对智能传播的信任度与接受度也在同步提升。[10]
2025年,智能传播已经进入了“主流化”的新阶段。对此,学术界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众声喧哗”式的回应。除了传播学者,来自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乃至未来学的学者们打破了学科边界,以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方式,调动理性能量,试图捕捉这场变革的本质。中国知网(CNKI)数据显示,国内以“智能传播”为主题的文献产出量呈现“J型曲线年起步,历经数年的技术发酵,在2025年迎来了井喷式增长,年发文量突破650篇,智能传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主流热点之一。智能传播显然是新闻传播学科观察人工智能浪潮的特别视角。因此,在学科分布上,“新闻与传媒”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贡献了超过52%的文献量,同时也延伸至“自动化技术”“计算机软件”“文化”“高等教育”以及“工业经济”等广泛领域。智能传播概念还有待“破圈”,才能进入更多的学科与领域。这也是对整个学科概念原创性能力的一次新检验。
通过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2025年智能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呈现清晰的“中心—边缘”的纵深结构。其中,“人工智能”“智能传播”“大模型”位于中心位置,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层,表明学界对底层技术驱动力的关注从未减弱。“国际传播”“新闻传播”“主流媒体”“媒体融合”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揭示了当前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AI技术解决具体的传播痛点,特别是在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方面的实践探索。“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传播风险”“人才培养”等议题的凸显,则标志着研究视角已从单纯的“技术赋能”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审视”。学界开始深入探讨机器主体性确立后的伦理困境、算法治理挑战以及新闻教育的范式转型。
在2025年的关键作者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一批具有高影响力的核心学者群。以方兴东、黄楚新、陈昌凤、彭兰、匡文波等为代表的领军学者,不仅在论文产量上保持领先,更通过广泛的学术合作形成了紧密的知识网络。他们或聚焦于智能传播的治理逻辑,或深耕于人机传播的伦理边界,或探索大模型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共同谱写了中国智能传播研究的理论交响乐。这种“众声喧哗”而又“和而不同”的学术生态,为理解2025年这一主流化元年提供了基础性的认知框架。
将视野拓展至全球学术场域,Web of Science(WOS)数据显示,以“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为主题的国际文献产出在2024年达到新高(6090篇),2025年为5478篇,并未出现中文学术界的高速增长态势。这并非意味着国际学界对智能传播的关注停滞,而在于中外使用术语的差异。在WOS的理工科主导语境下,“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更多被定义为通信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如6G网络、自组织网络与边缘计算优化。随着底层通信技术的逐步成熟与标准化,纯技术维度的研究进入Gartner曲线的“成熟期”。同时,智能传播的研究也与“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HMC)”“计算传播(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共振。在国际学界,特别是以Guzman Andrea L、Oehl Michael等为代表的学者在HMC领域对“机器作为传播主体”的探讨,为智能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计算传播学所强调的数据驱动范式,也为智能传播的效果评估与舆论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智能传播的主流化,实际上也是这些相关领域在智能时代的一次理论合流。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在2025年的趋势增长,更多是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回响”。国内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DeepSeek等大模型对新闻生产、社会治理及伦理规范的冲击,将“智能传播”这一概念迁移至人文社科场域,从而激发了新一轮的学术增长极。
因此,综述2025年的智能传播研究,不仅要记录AI普及的宏观数据,更需深度剖析当智能传播跨越鸿沟、进入早期大众阶段时,整个学术领域的思想焦点、研究范式与价值关切发生了何种战略性转向。这一时代背景不仅为我们理解技术和应用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框架,也为我们检阅学术界的敏锐感和思想力提供了检验标准。综观2025年的学术图景,研究已从早期对技术可能性的惊叹,全面转向对“主流化现实”的深刻介入。研究重心的迁移,正是学术共同体对“主流化”进程最自觉的回应。本次综述旨在锚定这一转折点,它既是对智能传播成为主流社会事实的年度见证,也是对其未来将塑何种传播秩序与人类境况的一次前瞻性思考。
2025年,在DeepSeek开源等事件的推动下,智能传播掀起主流化浪潮,机器作为内容生成和发送的新型主体地位开始确立。“AI生成内容首次超越人类创作,占互联网书面内容的52%。”[11]这一里程碑事件,第一次全面挑战了人类对内容生产的绝对垄断权,AIGC成为信息传播新的主导力量。回顾过往传播体系,人类主体性理所当然占据着绝对主导位置,无论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还是香农·韦弗的信息论,都始终将机器界定为无自主意识的工具。然而,随着智能互联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工具的普及应用,传播实现了从“人—人传播”到“人—机—人传播”,再到“机—机传播”的范式演变。这一传播的主体性的转向,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受到深刻挑战,机器在传播活动中的独立价值与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在国际传播学界,“人机传播”(HMC)研究兴起,致力于探讨人类如何与机器进行意义生成的交流,挑战了传统的“计算机中介传播”(CMC)范式。机器作为“传播者”主体地位的讨论,成为2025年学界对人机关系与智能传播探讨的关键议题。
首先是对智能传播范式变革本质的揭示。智能传播范式的跃迁,并非简单的技术线性升级,而是传播本质的结构性变革。方兴东等通过梳理大众传播范式、网络传播范式、社交传播范式、智能传播范式四大信息传播范式的演进逻辑,系统性地揭示了范式转型的核心驱动利益变化与发展趋势,分析了智能传播范式所牵引的整体传播体系的深度重构。[12]在此体系中,机器作为技术行动者,从过去被动响应的“中介”身份蜕变成为能够主动发起传播、自主进行内容生产、动态优化传播策略的“独立行动者”。徐帅结合当前数字新闻中的技术应用实践,指出数字新闻的发展,正在打破传统行动者网络中的“人类—非人类”二元边界,催生出人机深度融合的混合主体行动者,技术从被动的工具变为参与意义共建的“主体编程者”。[13]涂凌波等人结合智能传播技术演变,探讨了数字新闻活动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所共建的技术系统,看到了在新闻业发展中机器主体的运作与参与,以及所引发的数字新闻业个体、组织和生态层面上的结构性变革。[14]除了新闻业的具体实践层面,机器主体性确立所引发的智能传播结构性变革,还体现在人机情感交互模式上的结构性转变上。例如,赵静宜通过剖析从基于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CASA理论,到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的MASA理论,分析了所发生的人机交互方式与情感传播交流转向变化,强调机器已经成为具备生命属性且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其对复杂的情感具有识别和表达功能。[15]这些研究都昭示着,智能技术的发展重构着当代信息生态的底层架构,引发了现实层面的深度思考。机器主体性的确立,并未否定人类的传播主体地位,反而搭建起了“人类—机器”双主体共生的新框架。两者协作,共同塑造着新的信息生产与流通秩序。
其次是对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概念和理论化确立。易前良在探讨人机传播的过程中,将机器定位为传播者,探寻人类与机器共生的生产意义,通过梳理机器从“交互行动者”进化到“交互主体”的知识脉络,拓展出了“人技(机)共生”的新理论框架。[16]还有学者从价值哲学与社会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新的转变下人机关系的重塑,以及面临的深刻社会伦理挑战。例如,Zhang XS提出了“人主导的有限主体”的理论模型,探讨人工智能从“客观化的工具”向“受限主体”转变的轨迹,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从单纯的工具演变为“准主体”,为在社会伦理框架下定位人工智能的准主体角色奠定了概念基础。[17]Chen D等人结合当前人机协作在国防、医疗保健和自主系统等领域通过整合人工智能驱动决策、信任校准和自适应团队协作方式,从社会伦理视角进一步强化了人工智能决策内在理论模型与概念。也有学者关注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工具所推进的人际传播理论框架的演变。[18]例如,潘文静着Kaiyu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探讨了如何构建人工智能在人机传播理论框架中的主体性,指出人工智能是超越工具性的存在,传统人机传播理论已不再适用于智能传播时代,并认为这是人机传播探索的关键。[19]同时,也有学者进一步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智能传播的基础上搭建理论框架、探索概念外延。林克勤等人立足于智能传播的发展技术逻辑,结合人工智能行为主义的主流,洞察人工智能在信息生产流通中由认知工具到认知主体的角色定位嬗变,探讨了在机器主体性确定下,智能传播在认知理论框架上的延展。
再次是对AIGC的规模化应用对传播格局颠覆的探讨。AIGC内容的迅速增长以及机器传播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引发了学术界对内容生产权力结构的集中探讨与深度反思。传统观点更多认为内容生产的权力源于人类的创造力与话语权,其中精英阶层通过对媒介资源、专业技能的垄断主导着社会主流叙事的建构。而在AIGC时代,人工智能叙事系统确立,传播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蒋晓丽等人以DeepSeek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对人机传播关系、认知边界、认知基础设施架构的革新,指出了AI普惠性发展对于全球人工智能传播生态的重构,以及全球传播生态所呈现的新质传播力、强情感投射、技术民主化、传播主体间性四个特征。[20]此外,媒介变革日益突破人类的叙事想象边界,带来了认知革命演进下的传播叙事系统变革。例如,战迪等从共生到进化的视角,指出技术自主系统与人类认知需求是根植于技术物质基础的递进互构关系,智能装置驱动下的内容自主生成与分发模式重组了智能叙事效能,以想象进化推动智能叙事与技术文化的新发展。[21]Lucas-Moreira O D等人观察到人工智能时代叙事方式的深刻变革,以及人类创造力与机器创造力之间界限的日渐模糊,考察了机器生成的内容如何挑战传统的作者身份、创造力和意义建构观念,探讨了数字媒体时代人类主体性及其在与智能系统共同塑造叙事过程中不断演变的角色。[22]
最后是学界对新涌现的“机器”传播者主体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前瞻性思考,这为未来智能传播范式确立了现实指引方向。同时,2025年AIGC对传播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影响,超越了简单的传播力量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权力再分配博弈。AI虽然通过自主生成与智能分发获得了对信息叙事的表层主导权,但其实质上仍然离不开人类对数据与算法规则的掌握,需要从伦理、认知革命、技术哲学等方面深化考量人机共生的主体博弈关系。
如果说AIGC规模化应用确立了“机器”作为传播者的主体地位,那么智能体的崛起与“跨人类传播”范式建设,则进一步推动了“机器”作为传播者从“对话者”到“主体参与者”的关键能力跃迁。这从技术和应用的基础层面印证着主流化元年的到来,以及作为传播主体的机器对以人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学基本范式的冲击。2025年11月,Google DeepMind发布的Gemini 3取得突破性进展,在Humanity’s Last Exam测试中无工具状态得分37.5%,启用增强模式后飙升至41%,远超GPT-5.1的26.5%。这个突破标志着AI界即将进入“共建AGI”新阶段。[23]具备推理与代码能力的智能体正在改变智能传播链条,构建起人与AI共生的新型社会关系。
从智能体崛起的维度,不少学者聚焦智能体的发展,探讨机器如何实现从“被动响应指令”向“主动创造价值”转变。一方面,智能体的应用激发出智能媒介传播新潜能。智能体以主动意图识别与行动执行能力,将传播与行动深度融合,在新的场域中开展媒介实践。孙玮等从计算维度的媒介学出发,发现在智能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交互下,智能媒介的调节性跃入新的阶段,个体化智能体的应用激发了Web3.0的主体动能,推进了可编程社会实践的大规模开展。[24]赵子忠等从传播学的视角解读智能体,深入探究其对大模型智能传播体系的影响,指出智能体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不仅搭建了提供多模态内容的用户交互传播系统,更作为智能传播主体,在新系统中构建起智能内容生产新流程与用户交往新模式。[25]
另一方面,智能体调节着现实世界与个体的观念、认知感触。技术交互巧妙地影响着传播链条的变化,以技术可供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嵌入用户的认知塑造过程中。刘涛指出,作为智能体的AI,在智能传播中以合作的、对话的、共创的主体形式出现时,人与机器之间互为“镜像”,形成人机混合的新兴智能形态,拓展着现实世界的表征与认知空间。[26]而牟怡等人则从实证的角度,以量化分析方式发现智能体对于个人认知的调节以及个人与智能体和虚拟人的深度意义交互,能正向预测青年对于数字生命的接受度,从而完成智能传播技术对现代青年生死认知与价值观念的动态重塑。这些现实性的分析不仅展现了智能体与智能传播的深度融合,更凸显了其在社会系统运行中的重要价值。[27]
更为重要的是,智能体不仅改变了传播链条及其功能,更催生了“跨人类传播”这一新型传播形态。在智能传播主流化的趋势下,“跨人类传播”的学术合法性在2025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融入社会的常态化存在。方兴东等指出智能体不仅推动了人机传播,而且嫁接到人与物的传播,甚至也将全面改变人类传播的内涵和外延,推动着传播从人类中心向多主体协同的生态系统转变,形成“跨人类传播”的新传播格局。[28]这种超越物种界限的传播活动,其核心特征是传播主体的异质性与传播关系的共生性。林爱珺等人打破传统主客二元对立视角,从“共在—共通—共协”的视角切入,观察在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过程中,智能体如何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以人机协同的方式展开传播活动,为由智能体所主导的新型传播中人机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合理性。[29]可以看出,智能体已被纳入人类的社会网络,成为具有角色期待与社会规范约束的“共存者”,其传播主体地位的学术研究价值凸显。郑满宁通过分析分布式训练、对抗生成、联邦学习等机器交互技术路径,发现了人工智能技术所催生的以“机器交互”为核心的新型传播范式,以及传播生态从“人—人”“人—机”二元关系到“人—机—机”三元嵌套系统的转向。[30]
在“跨人类传播”常态化发展之下,人与AI共生的新型社会关系也引发关注,智能体崛起背景下的人机交互中,人的主体性何去何从成为热议话题。彭兰指出,在算法、大模型等智能传播技术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关系模式发生变化;当算法用新的逻辑重构文本之间的关系时,也推动了新认知连接的产生。[31]新的传播形态下,信息的流动与传播不再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意图,而是依托于海量数据的智能匹配与算法的深度分析,自我主体是否会就此湮没引发广泛思考。Berg M指出人工智能并不是仅仅模仿人类的认知,需要将其定义为社会技术结构的积极共同创造者,其文以能动性和动态的方式强调了人工智能在社会与技术领域中的嵌入性,认为如何看待涌现的社会技术自我成为理解人机交流的关键。[32]殷乐等人通过从“主体性感知机制”“他者角色功能”“语言秩序开放度”三个维度对ChatGPT、DeepSeek、豆包等大语言模型进行多案例交叉分析,发现智能体会在对使用者进行反身化的凝视中,构建自身语言秩序圆满化的方向,造成使用者主体性的结构性缺场,未来可通过提升使用者的AI素养,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运营与监管中建立全链条的伦理规范等方式,为使用者的主体性回返创造条件。[33]
综上所述,智能体的崛起与“跨人类传播”的常态化探讨,是2025年智能传播主流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智能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全面革新。这一变革不仅为智能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与视角,也带来了诸多现实性发展问题的持续探索。推动智能传播体系的持续完善,为人类在“跨人类传播”时代如何保持主体性与社会韧性提供发展路径。
2025年被视为智能传播从“概念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转折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人,较2024年12月增长2.66亿人,普及率达到36.5%。[34]这意味着,每3个中国网民中就有1个把大模型当成日常“标配”,生成式AI正快速融入中国用户的日常生活。还有调查指出,中国用户使用生成式AI的主要目的包括回答问题、日常办公(如会议纪要撰写、PPT制作)、休闲娱乐和内容创作等。[35]其中,“回答问题”的用户占比最高,达80.9%。这一社会化渗透态势,推动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从早期的“技术可能性”转向了更为紧迫的“生存现实性”,围绕着劳动生产、医疗伦理、教育认知、情感陪伴等核心生活场域,揭示一种深度嵌入、人机互构的社会新图景。
在劳动与创作领域,智能传播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深刻重塑了职业身份与人机关系。一方面,AI赋能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与文化传播模式。在农业生产中,李怀苍等指出数智化技术催生了“新农人”群体,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这种“AI+直播”模式通过“三脉合一”模型实现了农业品牌从销售向文化IP传播的转型。[36]在文化档案领域,周林兴等提出智能技术实现了档案资源的“数据化、体验式、场景式”传播,构建了新的文化传播空间。[37]另一方面,人机协作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在短视频创作中,丁方舟等发现人与AI的关系已超越主客体对立,演化为“驯化、诠释、它异、互构”四种形态,AI深度嵌入创作流程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创作思维异化的担忧。[38]这种异化在出版与翻译行业表现为一种职业危机,AI翻译虽然提升了传播效率,但也迫使译者面临“去技能化”风险,不得不向“译后编辑”等高阶应用转型。[39]对此,牛晓光强调了人工主体在“核查AI结果、监督AI流程”中的核心地位,以维持人机协同的平衡。[40]
医疗是AI应用最为深入,但也是最为敏感的领域,技术红利与伦理风险并存。朱文珍等指出大模型已覆盖从病历生成、影像辅助诊断到药物新靶点发现的全流程,显著提升了诊疗效率。[41]然而,这种深度介入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医患关系,形成了“医生—AI—患者”的三元结构。张如意等认为AI的“黑箱”特性和缺乏同理心的程式化特征,可能导致患者在面对医生与AI意见分歧时出现“决策瘫痪”。[42]更为严峻的是,算法偏见(如种族/性别差异导致的预测偏差)、算法误判及隐私泄露风险日益凸显,这迫切要求建立明确的误判责任机制,确立AI的辅助地位,防止技术“家长式作风”削弱患者自主权。[43]
教育领域正经历着由AI技术引发的深层震荡。国产大模型DeepSeek的迅速普及引发了教育领域的“蝴蝶效应”,陆道坤指出它不仅倒逼教学内容从知识灌输转向思维培养,更促使师生关系从“师道尊严”转向“机师—学伴”的生态。[44]然而,这种便捷性也引发了对学生主体性危机的担忧。学界警示,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学生“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的弱化,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45]同时,常歌等指出智能推荐机制可能导致大学生陷入“信息茧房”,造成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主题错位”。[46]面对技术迭代,王琼等指出现有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显现出“数字有余、智能不足”的结构性短板,缺乏对底层算法逻辑的深度教学,难以培养出真正驾驭AI的复合型人才。[47]
AI深度介入人类的情感生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准社会关系”。一方面,田浩发现用户通过“捏崽”(定制AI人格)或与虚拟偶像互动,寻求情感陪伴和心理支持。这种互动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智能人格养成实践”,并构成了能够实现现实亲密关系补偿的“超人际互动”[48]。另一方面,这种人机共情机制也伴随着风险。郝祥军等指出,AI虽然通过识别用户情绪并给予反馈,形成了类似人类的共情体验,但这可能构建出一种“情感温室”,导致个体对现实情感体验的忽视。[49]此外,当AI表现出“失智”或“失控”时,用户会产生强烈的“AI焦虑”,折射出人对技术控制感的丧失。[50]
在宏观社会层面,智能传播的应用改变了舆论环境,也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51]面对舆情“失真”和“突变”的风险,陈鹏宇提出应根据舆情发展萌发、发酵、成型的不同阶段,应用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并坚持“四个有利于”原则,利用AI进行实时监测与决策支持。[5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传播环境下“躺枪”现象(无关主体被卷入舆论)频发,这源于信息源头失真和算法推荐偏差,成为治理的新难题。[53]在公众认知层面,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AI持务实的“工具导向”,对实用型AI(如家务机器人)接受度高,而对涉及社会情感关系的AI接受度较低。[54]这反映了公众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对人机边界仍保持着本能的审慎。
在AI应用高歌猛进的背后,学界对智能传播引发的深层隐忧也表达了强烈关切。一是认知能力的退化与“脑腐”。余胜泉指出,过度依赖AI进行“认知外包”可能导致学生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思维趋向肤浅化与碎片化,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外包陷阱”[55]。李培根进一步警告,这种便利可能带来“认知负债”,即短期内解决了问题,但长期来看是以牺牲高阶思维能力为代价的。[56]张庆园等则引入了“脑腐”(brain rot)这一概念,描述了因长期摄入低质量、短平快内容而导致的认知能力退行,这本质上是技术加速主义与人性需求失衡的产物。[57]二是认知域的异化与“算法黑箱”。林克勤等分析了智能传播中的“认知域”,指出智能系统虽然模拟了人脑的信息加工,但其“模块化”特征和“黑箱逻辑”可能导致认知过程的异化。[58]马忠等强调,生成式大模型内嵌的认知结构可能会潜移默化地重塑社会认知,带来“认知倾向的技术操控”和“社会认知的虚假状态”风险。[59]三是认知结构的失衡与“去智化”。汪凡淙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过度依赖AI(低绩效组)会导致认知结构松散、交互行为单一,而有效利用AI(高绩效组)则能形成均衡的认知结构和高效的交互模式。[60]这表明,AI既可能赋能,也可能导致“去智化”,产生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个体的先前知识水平和元认知能力。董剑桥则区分了“认知卸载”与“认知外包”,指出如果不加辨别地将核心认知任务外包给AI,将面临“主体失能”的风险。[61]四是信息识别的困境与信任危机。金帆等的研究显示,用户对AI生成图片(AIGI)的识别准确率并不高,仅约58%,且普遍持怀疑态度。[62]这种识别困难和不信任感可能加剧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混乱和信任危机。
综上,2025年智能传播所展现的广泛渗透与伴生的隐忧,标志着技术的普及不仅是用户数量的攀升,更意味着其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深度介入从个体认知到公共治理的各个核心领域。学界对“脑腐”“算法黑箱”“情感温室”等隐忧的集中审视,恰是对其已成为主流社会事实后所必须开展的规范性校准。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伦理共识与人文反思驾驭智能传播的巨大潜能,约束其潜在风险,是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
2025年,智能传播的主流化进程不仅体现在国内社会的深度渗透,更体现在国际传播场域的结构性重塑。2025年11月10日,Meta发布了Omnilingual ASR全语言自动语音识别系统,支持1600多种语言,其中包括超过500种此前从未被ASR系统支持过的语言,为全球跨语言传播提供技术基础。[63]语言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载体正在经历数字化重构,智能传播已成为驱动全球信息流动的新引擎。智能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同频共振呈现鲜明的新特征:一方面,AI翻译打破了传统人力翻译的时空局限,大幅提升了跨语言信息转换的效率与广度,使得边缘语言和弱势文化在数字空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智能传播也带来了“数字帝国主义”加深的风险,拥有数据霸权的跨国科技巨头可能会通过算法偏见强化某种单一的文化叙事,导致全球传播秩序的失衡。
围绕这一新议题,学界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入考察。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场本体论层面的范式革命。传统的“中心—边缘”依附理论和单向度的“走出去”模式,正被一种基于连接与共享的新范式取代。2025年DeepSeek等开源大模型的崛起,被视为打破硅谷技术垄断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推动国际传播向“全球共通”转型。[64]方兴东等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全球共通”作为国际传播核心理念的创新,强调超越传统跨文化传播框架,构建新的知识体系。[65]随着技术与社会的深度互嵌,国际传播进入了“深度交往”时代。张毓强指出,这要求中国国际传播从“以中国为方法”向“以世界为目的”转型,通过“数字共通”机制,在基础设施、信息数据、文化意义和主体间性四个层面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对线]
面对“西强中弱”的舆论格局和数字平台的“围墙花园”,如何利用智能技术实现体系化的突围成为关键议题。陈积银等人认为,智能技术为破解“受众模糊”难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多源数据挖掘和用户画像技术,国际传播正从“漫灌”转向“滴灌”,构建起包含主体、内容、话语、平台、受众、评估等子系统的精准传播生态。[67]尽管Meta等跨国巨头发布了全语言系统,但“数字帝国主义”和“数字边界”依然存在,信息流动仍受到算法偏见和地缘政治的隐性控制。因此,有学者强调必须打破“借船出海”的路径依赖,利用技术变革的窗口期,推动TikTok、Temu等本土平台“造船出海”,在社交、电商、游戏等领域抢占国际传播的舆论高地,构建自主可控的平台生态。[68]
在智能传播时代,传播主体从国家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内容生产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情感与文化共生。付李琢指出,网络文艺的国际传播正从“出海”迈向“共生”,其核心在于实现“主体间性”。通过粉丝社群的交互共创,海外受众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69]这种“交互主体性”强调承认他者文化的独特性,在对话中实现意义的协商与价值共创。以《黑神话:悟空》、李子柒视频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品,通过“审美共通”和“情感共通”超越了语言障碍。匡文波认为,这些产品利用智能技术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构建了“共融共情”的叙事模式,使抽象的文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经验。[70]在多极化背景下,国际传播正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通过区域国别研究视角的引入,中国媒体在报道非西方国家议题时开始构建差异化的“去西方化”话语,推动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
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伦理风险,“反共通”力量正在崛起。如何在技术赋能中坚守人文精神,成为国际传播的底线问题。曾艳钰强调,AI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文化遗产保护和跨语言传播的效率,但必须坚持“人文精神”的主导地位。[71]AI应作为辅助工具,而价值判断、情感传递和历史解释的主体性仍归属人类。必须警惕算法导致的文化同质化和“知识伪造”风险。罗幸等指出,算法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区域国别传播内容的偏颇,甚至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因此,构建人机协同的审核机制,设立高标准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打破技术垄断,是确保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真实性与公正性的必要手段。[72]
综上所述,2025年,智能传播已经成为重塑全球传播秩序的关键力量。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技术浪潮,突破了既有的技术垄断格局,在本体论层面推动“全球共通”成为超越地缘博弈的价值范式。这一主流化进程驱动传播体系向智能化、精准化全面转型。在文化交往维度,智能赋能的“主体间性”与“共生”模式,促使数字文化产品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构建起深层互动的“数字共通”空间。与此同时,针对“数字帝国主义”与算法伦理风险的治理研究也占据重要位置,确立了科技与人文融合、人机协同治理的底线年国际传播研究的新图景。
2025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面下沉,智能传播的主流化进程迎来了一个关键的空间转折点,从数字空间的“在线”(Online)连接,演变为深度嵌入物理现实的“在场”(On-site)共生。在前一阶段,智能传播主要体现为通过屏幕进行的符号交换。孙玮与於春的研究均指出,无论是“传递观”下的话语实践,还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离身计算,身体在传播中或是被视为阻碍,或是仅作为缺席的在场。[73][74]早期虚拟主持人,如2000年的“安娜诺娃”,正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依靠真人配音或符号计算生成形象,却始终被禁锢在屏幕的二维世界中。2025年3月18日,英伟达CEO黄仁勋在GTC 2025大会上明确提出从“生成式AI”向“物理AI”的演进路线,正式宣告了“物理AI”时代的到来。而与“安娜诺娃”的“离身”屏幕形象不同的是,2025年春晚舞台上,16台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在场”共舞,证明机器主体已经具备了在物理现实中进行“非符号性交流”的能力。智能体从处理信息的“大脑”进化为具备行动能力的“躯体”,传播的介质也从流动的比特凝固为可触碰的原子。
这一从“离身符号”向“物理实体”的本体论转向,标志着智能传播的技术逻辑与实践场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面对产业界“物理AI”的崛起,2025年的学术界迅速做出了敏锐且深刻的理论回响,构建了一幅系统性的具身传播知识图谱。首先,在宏观范式层面,学界确立了“空间”与“具身”在智能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喻国明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空间传播范式”,指出媒介的功能已从传递信息的载体升维为能够感知、理解并响应三维物理空间的“环境模拟器”与“认知接口”,具身AI的本质即“把AI装进身体,而非关进屏幕”。[75]这一论断得到了薛可等的呼应,他们构建的D-PEICA模型强调“具身化数字持存”,认为身体以数字化身形式在虚拟空间中的永存与知觉延续,是构建数字信任与联盟的基础,从而摆脱了离身语言交流的“对空言说”困境。[76]潘文静进一步将“具身性”确立为AI主体性四维结构的核心,指出物理实体的“在场”直接重塑了人类对机器的归因逻辑与信任模式。[77]
其次,在哲学本体层面,研究者深入考释了具身智能如何改变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以及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的本体论地位。肖峰敏锐地指出具身智能标志着AI从模拟思考的“认知AI”进化为模拟行动的“行动AI”,并提出了“赛博身体+赛博智能”的终极构想,挑战了传统的生物保守主义人类观。[78]吕清远则从身体现象学视角出发,提出技术媒介“存在于肉身之间的行动者与机能体”,它通过“感官在场”“意识显现”与“行为习得”构造自身的“身体图式”,实现了对人类行为模式的“惯习定向”。[79]常江等通过梳理具身智能从“分离型”到“缔合型”的演进,警示了由此带来的“全景敞视”风险,即生活世界被简化为供机器运行的向量化程序界面,主张通过“数据行动主义”来重塑人类文明韧性。[80]
最后,在微观场景层面,学界致力于利用具身智能修复被“离身传播”割裂的认知与情感体验。针对生成式AI带来的“离身学习”危机,洪玲呼吁回归“具身立场”,在人机协作中重建认知的具身性。[81]袁小群等则提出通过“具身交互”重构数字叙事,实现从“身体操作界面”到“身体驱动叙事”的跃升。[82]在跨文化与情感交往领域,吴志远提倡从“身临其境”走向海德格尔式的“设身处境”,强调身体与技术环境在存在论层面的一体性。[83]曲茹等提出的“具身—转译”耦合机制,旨在推动传播从“数字孪生”的视觉奇观转向“身体在场”的意义共创。[84]而孙菡忆等则在仪式观的重构中指出,技术具身虽实现了感官延伸,但也需警惕感官过载对仪式神圣性的消解。[85]
综上所述,2025年智能传播的具身转向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学科认识论革命。学界不仅在经验层面确认了传播介质从“屏幕符号”向“物理实体”的迁移,更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双重超越。一是超越了“身心二元论”,确立了身体在认知与传播中的本体论地位;二是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承认了技术媒介作为独立“机能主体”的行动能力。在这一主题上,学界关于“空间传播范式”“机能主体”与“感知身体”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从学理层面阐明了智能传播已不再是外在于日常生活的技术工具,而演变为深度嵌入物理时空与感官结构的社会基础设施。这种从“符号表征”到“实体实践”的质变,重塑了人机交互的基础形态,确立了智能传播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主流化地位。
2025年,人工智能平台以爆炸式姿态扩张,在人类技术发展史上这样的技术普及速度几乎前所未有。短短三年内,独立人工智能工具的用户数量就达到了传统社交媒体平台十多年才达到的水平。[86]这一历史性转变,让智能传播从技术圈层的专属工具下沉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通用基础设施,重塑着信息生产与分发的底层逻辑。然而,主流化的加速推进也伴随着治理体系的适配性危机,如何解决“真假难辨”的信任赤字问题,成为学界对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探讨的核心所在。治理正从“内容规制”转向“技术之治”,倒逼着学术界从早期的风险预警转向治理路径的系统性构建,形成跨学科视角下的技术、制度、伦理协同治理思路,以及应对人工智能主流化挑战的核心共识。
首先,针对“真假难辨”的信任赤字,AI幻觉成为学界面向主流化治理的重要关切。Robles P等指出公众信任是良好的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框架需考虑公众对人工智能政策的信任情况。[87]从信任赤字的技术根源来看,当前主流AIGC模型多数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训练模式运行,其内容生成过程依赖海量数据的特征提取与算法参数的动态调整,容易产生幻觉问题,诱发人机信任危机。张梦晗等人以实证的方式提炼出数据操控、透明性失准、舆论多元性冲击等三大核心风险表征,探索了由于训练数据源头性污染、治理机制碎片化、技术发展军备化及AI内容辨识困难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AI发展结构性失序问题,提出了未来风险治理的可能性实践路径。[88]庞华探讨了技术权威遮蔽、跨模态误导与算法流量裹挟模式下伪真叙事的生成逻辑,以及大语言模型催化下公众参与“失真”内容的传播扩散情况,旨在建立敏捷治理机制,防范AI幻觉对公共认知理性的侵蚀。[89]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所存在的幻觉问题成为制约其可信性与安全性的重要隐患,郭全中等人指出面对幻觉的多发易变,通过构建模型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分层对象治理体系、创新政策治理体系等方式形成“敏捷治理”体系,成为AI幻觉治理的有效路径。[90]
其次,去中心化的开源生态与中心化监管之间的张力成为AIGC治理的核心矛盾。方兴东等指出DeepSeek通过成本、效率、开源等系统性工程创新,推动AI成功跨越主流化鸿沟,引发技术、商业、社会和政界的强烈反响。[91]大模型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着AIGC技术由大企业垄断走向普惠化应用。但开源生态的无边界性,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Ghosh A等人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在提供卓越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大威胁和伦理问题,AI大模型广泛应用下的问责机制缺失和算法偏见需被重视,对偏见、透明度、经济影响以及适应性监管Kaiyu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方法的必要性探讨,是构建人工智能治理理论框架的关键所在。[92]同时,与传统舆论场相比,由AIGC主导的智能传播生态舆论呈现新的风险特征,对公共领域的理性对话构成挑战。董天策指出智能传播全面刷新网络舆论空间,信息传播与舆论生态正处于旧秩序已打破、新秩序未建立的时期,这使得智能交互背景下的舆论生态日益复杂,需以制度、技术、主体的多元协同构建新的治理体系。[93]赵蓓等人从关系建构的视角出发,探讨智能传播时代舆论生态治理的新范式,从治理结构、治理逻辑、治理理念等多个层面,回应智能传播时代舆论生态治理的复杂挑战,将舆论治理视为一种动态的关系调节过程,来重构治理路径。[94]这也就意味着当前智能传播舆论生态所面临的治理问题是流动的,正在诱发新型舆论风险,带来治理上的舆论挑战。正如张文祥所指出的,智能传播时代舆论生态所出现的舆论载体“武装化”、舆论主体“脱域化”、舆论客体“失控化”等异化特征,割裂着舆论事实的认知途径,操纵着舆论话语的公共导向,绑架着社会信任,需以多元主体的侧芽效应来破解顶端优势所带来的治理困局,消除新型舆论治理的悬浮状态。[95]
究其本质,当前智能传播治理的关键挑战,是AIGC技术传播生态的“监管滞后”问题。AI主流化的快速发展与历史性突破,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进入高潮阶段。方兴东等指出,AI技术正加速向智能爆炸式的临界状态逼近,AI失控的临界点可能就在当下,AI监管问题刻不容缓,需从社会、认知与存在多重维度来解析AI可能带来的灭绝性风险,构建AI治理新范式。[96]邓建鹏等人指出,AI发展的思维链和模型开源缓解了“算法黑箱”困境,为监管审查提供了便利,但其关于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技术创新与保护平衡、模型提示与反馈机制、模型安全性的问题成为新的监管重点,需要尽快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保障人工智能安全与良性发展。[97]治理需注重从“内容规制”到“技术之治”的跃迁,实现技术治理与技术发展的同频共振,主动将治理逻辑融入技术演进。Wang Y等指出大模型智能体相关的安全漏洞与隐私风险,考察了其底层机制与潜在风险,探讨了在未来智能技术治理中,构建安全的大模型智能体生态系统的必要性。[98]这是AIGC主流化背景下治理理念的根本变革,更是推动AIGC技术“生态重塑”的关键保障。
本文系统检阅了2025年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智能传播主流化的跨学科回响,勾勒出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学术图景。所谓“主流化元年”,其核心标志在于智能传播技术完成了从“创新者”向“早期大众”的跨越,确立了以“DeepSeek时刻”为起点的技术普惠化与基础设施化特征。在这一阶段,智能传播通过架构优化与成本控制消解了技术壁垒,实现了从“在线”符号交互向“在场”具身实践的演进,更在应用层面实现了“社会化祛魅”,成为嵌入生产与生活全流程的通用生产力工具。学术共同体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建设者,呈现非凡的创新力。学术界的研究焦点随之发生了结构性迁移,从早期对技术可能性的探索,转向对机器主体性确立、“跨人类传播”常态化以及去中心化开源生态治理等现实议题的深度介入。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智能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传播渠道的延伸,而是重构人类社会连接的基础架构与文明形态。
这场人工智能革命首先是传播革命,新闻传播学正处于范式转变的“震中”,呈现“系统性变革与系统性崩溃”同时发生的特殊张力。而这种张力也表明智能传播正处于“前范式阶段”——尽管其作为未来主流传播形态的前景已然明朗,但支撑其运行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尚未确定。一方面,传统的以人类为主体的传播学基本范式面临失效风险,学科必须打破原有的二元论框架,接纳“人—机—机”的三元嵌套系统,直面算法黑箱、认知异化与伦理赤字等伴生危机;另一方面,当机器不仅具备信息处理能力,甚至拥有行动能力,当算力、代码与神经科学成为传播研究的必要变量时,学科边界的消融已成为必然趋势。正因为知识体系尚未定型,在这场新知识体系的突破和“探险”中,新闻传播学应该主动担当,率先发力,成为跨学科探索的引领者。而置身于这一前范式向新范式过渡的系统性变革阶段,新闻传播学更得以站在人机文明共生的高度,为理解智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核心解释力,实现从对时代变革的单纯“回响”到对未来发展的主动“定义”的转变。这一历史使命必然也是新闻传播学辞旧迎新、全面实现系统性变革的历史契机。
[1]界面新闻.“AI的缔造者们”,《时代》周刊2025年度人物公布[EB/OL].
[2]方兴东,王奔,钟祥铭.DeepSeek时刻:技术—传播—社会(TCS)框架与主流化鸿沟的跨越[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4):126-135.
[3]谢新水.智能跃迁、开源创新与主权AI:DeepSeek现象推动人工智能开源创新生态体系建设[J].电子政务,2025(03):40-48.
[4]喻国明,金丽萍.生成式媒介的极致优化:DeepSeek对传播生态的系统性影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4):71-79.
[12]方兴东,王奔,钟祥铭.范式跃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路径选择——解析四大信息传播范式与传播格局之变[J].青年记者,2025(12):33-38.
[13]徐帅.谁是行动者?具身新闻中的混合主体及行动者网络重构[J/OL].新闻界,1-10[2025-12-22].
[14]涂凌波,马娅萌.可编程性:数字新闻生产技术系统的运作及其结构性变革[J].南京社会科学,2025(10):119-131.
[16]易前良.机器何以成为传播者: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拓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04):1-9+27.
[19]潘文静.超越工具性:人工智能主体性对人机传播的多维影响[J].编辑之友,2025(07):84-92.
[20]蒋晓丽,张宏凡.智能传播与中国路径:DeepSeek驱动人机共生的技术图景[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8(02):95-103.
[21]战迪,方杰云.从共生到进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的非对称演化机理[J].新闻界,2025(10):38-47+96.
[24]孙玮,张祁锴.智能体崛起:Web3.0的平台转型——兼论计算维度的媒介学[J].现代出版,2025(01):20-29.
[25]赵子忠,廖文瑞.智能体的传播学解读与创新[J].南方传媒研究,2025(04):57-65.
[26]刘涛.人机协作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叙事的“智能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03):67-83.
[27]牟怡,蓝剑锋.从“机事”到“机心”:“Z世代”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32(6):17-29+126.
[29]林爱珺,叶立.共在·共通·共协:人机传播的三重逻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5):151-160.
[30]郑满宁.算法共振:大模型交互视域下的传播主体重构与范式创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4):138-144.
[31]彭兰.智能传播技术驱动的“认知连接”[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1):71-78.
[33]殷乐,杜兴远.主体性的遮蔽与回返:人机传播视野下镜像机制运作的多案例分析[J/OL].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2[2025-12-22].
[3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R].2025:6.
[36]李怀苍,景永浩,武弘博.数智化赋能:民族地区农业品牌智能传播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2):156-166.
[37]周林兴,朱富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智能传播探析[J].北京档案,2025(01):23-30.
[38]丁方舟,张多.“AI只是你的工具吗?”——智能传播生态下短视频博主与AI的人机关系研究[J].新闻大学,2025(01):1-14+119.
[39]刘松.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现状、问题与展望[J].外语学刊,2025(03):20-25.
[41]朱文珍,吕文志,陈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J].放射学实践,2025,40(1):5-8.
[42]张如意,周运翱,彭迎春.“医生—医疗人工智能—患者”新型医患关系建构路径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5,38(1):103-108.
[43]吴腾.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智慧医疗建设的风险与规制[J].医学与社会,2025,38(3):9-16.
[44]陆道坤.颠覆与重构:DeepSeek引发的教育领域“蝴蝶效应”及应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4):144-152.
[45]周瑞冬,谢超凡.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人的主体性的挑战及应对[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5,41(2):100-110+133.
[46]常歌,任娟.智能传播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机理、挑战与进路——基于接受理论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25(02):31-39.
[47]王琼,吴起.智能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和进路[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78(2):76-87.
[48]田浩.“养成智能人格”:人机情感交往困境与AI焦虑生成[J].新闻与写作,2025(03):18-27.
[49]郝祥军,顾小清,柏宏权.人机何以共情:基于人机交往的情感连接与伦理反思[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5(03):79-87.
[50]斗维红.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依恋:虚拟偶像青年用户的情感依恋构成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5(01):86-93+85.
[51]周广立.AI传播视域下优化舆情应对工作的思路与实践[J].新闻前哨,2025(18):68-70.
[53]靖鸣,袁志红.误导、误传、误解:智能传播语境下的躺枪现象及其表征[J].新闻爱好者,2025(11):31-36.
[54]王俊秀.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状况研究——基于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20):35-47.
[55]余胜泉.跨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认知外包陷阱[J].中国教育学刊,2025(04):1.
[57]张庆园,刘欣桐.重拾认知主权与文明厚度:数字时代“脑腐”表征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对抗[J].南方传媒研究,2025(03):23-30.
[58]林克勤,张丽,郑继泽.论智能传播的认知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2):119-129.
[59]马忠,高怡英.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社会认知风险与应对[J].浙江社会科学,2025(02):95-105+158.
[60]汪凡淙,汤筱玙,余胜泉.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外包:交互行为模式与认知结构特征分析[J].心理学报,2025,57(6):967-986.
[61]董剑桥.认知卸载还是认知外包: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赋能与去智化风险[J].外国语文,2025,41(6):12-27.
[62]金帆,张鹏翼.社交媒体中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图片的识别与认知研究——识别准确度、依据与态度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5,48(6):12-19.
[64]何可,方兴东,钟祥铭.DeepSeek与全球共通——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挑战[J].当代传播,2025(02):16-22.
[65]何可,方兴东,林宇阳.全球共通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知识图景[J].对外传播,2025(01):14-18.
[66]张毓强,薛宇涵.中国国际传播研究2024:深度交往、平台社会与“共通”可能[J].新闻界,2025(02):84-96.
[67]陈积银,刘佳璇.技术赋能与生态形塑:精准国际传播体系智能化构建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3):149-160.
[68]赵永华,邹宇.技术生态、全球线年国际传播的新趋势和新议题展望[J].对外传播,2025(01):19-23.
[69]付李琢.从“出海”到“共生”:中国网络文艺国际传播的创新进阶[J].中国文艺评论,2025(03):63-75+126.
[70]匡文波,曹萩儿,张峰.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国际传播的范式转型与实践创新[J].中国编辑,2025(02):12-18.
[71] 曾艳钰.科技人文融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与国际传播[J].东吴学术,2025(01):81-87.
[72]罗幸,黄鑫磊.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J].传媒,2025(04):88-90.
[73]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40(12):83-103.
[74]於春.传播中的离身与具身: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认知交互[J].国际新闻界,2020,42(5):35-50.
[75]喻国明.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智能时代传播学范式革命下的几个重要概念解析[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1):1-10[2025-12-22].
[76]薛可,时伟.数字社交形塑对外传播新场域:构成特质、传播机理与行动路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1):75-84.
[77]潘文静.超越工具性:人工智能主体性对人机传播的多维影响[J].编辑之友,2025(07):84-92.
[79]吕清远.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与媒介权力的知识谱系考释——探访一种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32(2):36-49+126-127.
[80]常江,王鸿坤.作为媒介物的具身智能:演进过程与生态优化[J].中国编辑,2025(05):26-33.
[81]洪玲.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识学习的离身困境与实践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5):19-25.
[82]袁小群,李奕蓉.身体在场与认知延伸: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数字绘本数字叙事创新[J].出版广角,2025(08):78-84.
[83]吴志远.从“身临其境”到“设身处境”:论数字交往的身体观[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70(1):150-163.
[84]曲茹,张嘉印.从数字呈现到身体在场:具身智能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耦合机理与未来进路[J].中国编辑,2025(07):76-81.
[85]菡忆,苏玉波.具身传播视域下VR技术对春晚仪式观的挑战与重构[J].当代电视,2025(04):40-46.
[88]张梦晗,沈文乾.错位的升级与结构性失序:AI幻觉主导的信息迷雾风险与分类治理可能[J].传媒观察,2025(10):53-63.
[89]庞华.穿越AI幻觉迷雾:大模型伪真叙事的内生逻辑与敏捷治理[J/OL].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2025-12-22].
[91]方兴东,王奔,钟祥铭.DeepSeek时刻:技术—传播—社会(TCS)框架与主流化鸿沟的跨越[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4):126-135.
[93]董天策.智能交互下的舆论,该信任谁?[J].新闻与写作,2025(06):1.
[94]赵蓓,闫重宵,任吴炯.关系建构:智能传播时代舆论生态治理的新范式[J].新闻与写作,2025(06):28-39.
[95]张文祥.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的舆论生态挑战与治理进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1):155-164.
[96]方兴东,宋珂扬,钟祥铭.DeepSeek与科林格里奇困境: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机制及治理可能[J].新闻与写作,2025(05):51-59.
[97]邓建鹏,赵治松.DeepSeek的破局与变局: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4):99-108.
[陆舒怡: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董丽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方兴东(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刊学术顾问 ]
2025年,新闻传播研究立足数智技术变革与本土实践,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核心,在技术赋能与伦理治理中寻求平衡,为学科发展与行业升级提供了多元指引。
张志安 陈经伟:新闻业的数智化转型:技术吸纳与价值调适——2025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评